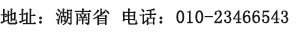汉口里份在操办完爷爷的后事之后,我和奶奶就被爸爸接到了汉口方正里,开始和我父母、弟弟一起生活。爸爸妈妈那间原本狭小的房间里,在增加了弟弟的童床后,就只剩下一条一米来宽的走道了。现在我和奶奶又来了,还真没处摆。不过好在爸爸早几年在房里搭了一个阁楼,可以作为奶奶的卧室。而我睡觉的钢丝单人床就摆在了那条走道上,晚上撑开白天收起来。至于做饭的灶具,则只好占用公共区域,移到了房门外通向后门的过道里。每到做饭时,奶奶都要提心吊胆,生怕会烫到来回穿梭嘻闹的小孩。而卫生间呢,别说是各家独卫了,就连整栋楼上下十来户共用一个卫生间都是妄想,整个方正里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各家都是自备马桶或痰盂,在自己房中解决问题后,到公厕中排队倾倒;夏天洗澡也是同理,也是轮流在房中洗,其他人在房外排队。这样的境遇或许是今天的孩子无法想象的。也许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不买套大些的房子,是没钱买吗?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是没有商品房这个概念的。城市里所有的房子都是公家的,由单位根据每家的人口数量来分配房源。我家的这间房是父母结婚时申请的,单位是按照两个人的标准分配的,所以比较小;既然是这样,如今人口增加了,就可以申请换大房子啊。是的,是可以,但前提是单位要有房可分才行。那个时候,城里的房屋资源比较紧缺,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很少,像我家这样的状况并非个例。我们要改善居住条件,就只能等待传说中的父亲单位上在建的福利分房了,但那还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这样的居住状况不管是对于此前三口之家的父母,还是习惯了琴断口老宅宽敞的奶奶来说,都是需要相当长时间来适应。不过还好,我并没有不习惯的感觉。因为,现在我每天都可以见到爸爸妈妈和可爱的弟弟,还可以每天看电视,更可以天天拉着奶奶,站马路边上看飞驰而过的各式各样的汽车。所有这些都是以前在老家无法享受的。而对于奶奶来说,最主要的还是爷爷去世所带来的悲伤。不管是陪我到马路边看汽车,还是在家空闲的时候,奶奶总是满面愁容,或者是以泪洗面。看到奶奶伤心,我也开心不起来,我能体会奶奶的感受,但是不知道怎样能让她释怀。于是我对她说:“您这就好比先被打了一巴掌(指堂叔去世)还没好,现在(爷爷去世)又打了一巴掌……”此话一下说到了奶奶的心坎里,她摸着我的头说:“我的儿,你硬说得我心里去了啊,我现在活着都觉得没意思啊……”“但是,太,您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呢?谁照顾我呢?您就着我看,想开点……”我这话果然见了效,成为了奶奶“转念一想”的理论依据,每当难过的时候,想一想我,她就会自我调节一下。后来就有人把我比喻为奶奶的拐杖。就这样,奶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我在精神上给奶奶的支撑,让我们祖孙奠定了深厚的感情。我和奶奶然而,也正是因为我和奶奶的感情至厚,也给家里造成了些许不和谐——婆媳战。我不说,您也能猜到,那就是我妈和奶奶之间因为在管教我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由此引发的摩擦。这样的情景很普遍,所以不必细说。但对于我来说,是最不愿意看到奶奶和妈妈这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之间发生不愉快。不过,难能可贵的是,她们之间的“战争”从来不会留后遗症,争过,吵过之后,谁都不会记仇,一切都会恢复如初。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妈妈在和奶奶的摩擦中越来越能忍让了。后来妈妈有一句听起来简单,但很有道理的话,她说:“争赢了,未必还能到哪里领个奖?”是啊,“清官难断家务事”,一家人之间的磕磕碰碰无可避免,也无需评是论非。如今奶奶已年过百岁,妈妈也是年近古稀,我也好多年没见她们“开战”了。看到她们现在能够坐在一起聊天,我感到非常欣慰!考虑到家里住房窄小,两位姑妈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轮流把奶奶接到自家小住一段时间。自然,奶奶不管去哪里,都不会落下我这个“拐杖”,我也更不可能愿意离开奶奶。因此,我自幼便和两位姑妈还有表兄表姐表弟们建立了不错的感情。这一天,爸爸应邀送我和奶奶到家住汉阳五里新村的大姑妈家。一到大姑家,我便拉着大我十多岁的表哥表姐们一起玩开了。大姑家住的平房,家门前有相对宽阔的地方可以供我们玩耍,而奶奶和爸爸就在屋里跟大姑和大姑父闲谈。但正当我玩得兴起时,爸爸突然从屋里走出来,来到了我跟前。我感觉爸爸神色有点不对,不待我问,爸爸就拉住我,先用手捂着我的右眼睛,问我:“看不看得见?”“看得见啊。”我不解地回答。爸爸又捂住我的左眼,继续问:“看不看得见?”“看……看不见!……”我的眼前一片漆黑,这才发现我的右眼已经失明!爸爸不肯相信地再三确认,但无情的现实没有留给他一丝幻想的空间。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眼睛为什么会在毫无察觉间失明?又是什么时候失明的?这个意外的结果让所有在场的人吃惊不已。“你的眼睛是么样瞎的?”爸爸连连追问我。我一时也不知所措,努力在记忆中搜寻答案。最终,我的记忆定位在了两年前的一天……那会儿爷爷还在世,父母每周末回来看我,同时还会带着我到同村的外婆家玩。国庆节这一天又去了外婆家,我和表弟表妹们正在后门口玩耍,听见妈妈在前屋叫我,我就赶忙往前屋跑。后门到前屋有一个过道,舅舅的自行车就停在过道上。我只顾跑,没留意那自行车,一不小心右眼撞在了自行车车头的把手上。当时眼睛很疼,但是看得见,肉眼也看不出有受伤的痕迹。妈妈时不时问我眼睛的状况,在得到我疼痛在逐渐减轻的反馈后,妈妈就没有特别在意。再后来眼睛不疼了,也就没有人在意了。而且,不懂事的我也并没有注意到双眼视力和单眼视力有什么不同,因而眼睛是什么时候失明的,我根本不知道。只是因为这是童年时期唯一的一次较重的眼睛碰撞事件,所以当发现右眼失明时,就自然联想到与这次撞眼有关。但是爸爸又是怎样未卜先知地知道我的眼睛出问题了呢?这其实是凑巧。那是前几天,我偶尔感觉眼前似有似无地有黑影晃动(其实就是闪光),觉得不解,于是跟奶奶说了一下。刚才他们聊天的时候奶奶提到了这件事,引起了爸爸的警觉,不料却有更意外的发现。本来愉快的姑家旅行因为这件事给搅了,所有人的心都因此被乌云笼罩了起来。特别是爸爸和妈妈,这个结果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他们对我未来的担忧势必加重了几层。他们带着我四处寻医,被诊断为视网膜脱落,但由于时隔太久,已无力回天。命运何其残忍,让我接受肢残的现实还不满足,更要补我一刀,将我拖入盲残的深渊……